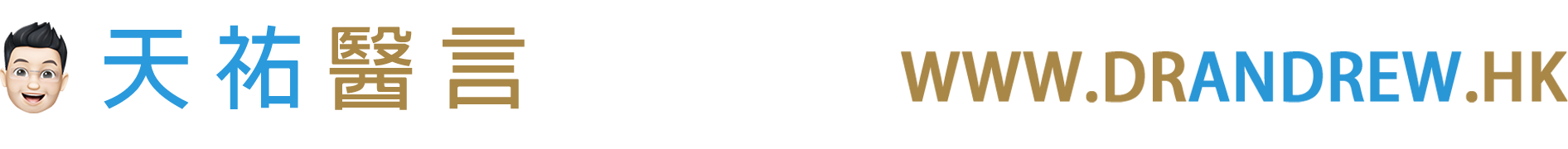「检疫」和「隔离」有何不同?
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会长
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
要有效控制传染病蔓延,公共卫生学常用的两个风险管理的措施为“检疫”和“隔离”,其实是有什么分别?
近期,在2020年初的检疫实例包括:
1.自二月八日之起,从中国内地来港之人士须进行家居检查疫14天;
2.停泊在日本横槟的「钻石公主号」邮轮乘客在船上进行检疫;
3.外国包机从武汉撤侨,回国后国民须在检疫中心或当地军营进行检疫14天。
而隔离示例包括:
1.怀疑及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应在医院内部隔离及进行治疗
2.正在接受检疫疫之人士出现病征时,需向有关方面求助,以做出隔离及诊断的安排。
从以上例子可以手术,检疫是针对一些没有症状的人,但他们曾接近接触确诊或疑似的患者;或他们曾到访传染病发病率较高的地区。检疫的目的是将他们与其他人如果他们不幸出现病征,可以将他们及早隔离接受治疗,并继续传染其他人。基本上,为了确认曾暴露于发生传染的地方之人士,在此传染病的潜伏期概括而言,检疫亦是一项可包括动物和货物流动限制的卫生措施。
其实,检疫措施在20世纪后期已逐渐减少并扩大了大规模地使用防控传染病工具,但由于新发病毒及传染病大流行如2003年的沙士,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症,2014年伊波拉病毒等等,国际间都使用了不同程度的检疫措施,并配合达致公共卫生水平以及临床的控制措施以控制疫情爆发。因为检疫包含限制及禁闭,所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病毒和人身自由的问题,怎样在公共卫生方面取得一个平衡点?当事件涉及和影响公众安全,我们就要考虑自由与人身安全的重要性。
初步检疫这措施的历史可追溯到1377年,当时没有有效药物可以控制医治扩大的鼠疫,以及18世纪后期用于处理霍乱疫情和20世纪初期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。在历史上所有的检疫行动和控制往往带有歧视,因为当时的生活水平,医疗科技,药物诊断等等都逐渐成熟,低下阶层以及社会边缘化之人士往往容易被标签为传播者,他们在没有选择下被禁闭于环境极差的地方隔离,所以这些人们都有望逃命离开,反而激增了疾病的散播。
诚然,现今的卫生检疫不可跟历史的方式同日而语,现时的措施是根据公共卫生的框架有效地执行,并根据流行病学的实证和科学标准,虽然在疫病蔓延的初期有很多变数,所以措施亦要不断更新,以迎合合对抗疫情需要;措施通常亦希望将被检疫者之人数减至最少。话虽如此,被检疫的人士的临时及社交活动,生理心理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。简单的例如不能如常上班,影响收入;需要照顾者如老人及小童怎样得到适切的照顾等等,这些很实际的生活问题,就要在计划实行检疫措施时作周全的考虑。显示出,从17年前沙士疫情中,分别在香港及加拿大多伦多接受检疫疫病的人,一部分人都出现了一些情绪,甚至患上伤口后遗症等心理问题。
另外值得再探讨的问题是,在一个公平社会里,当一小部分人的人身权利被牺牲以保障其他人之公共卫生时,是否应以既定机制,来补偿这些被检疫人士在金钱或非金钱上的损失呢?虽然某些国家检疫往往有当地的法律基础去支持,但实际实行措施时,不同政府用不同手法,以2003年沙士为例,当时加拿大是劝喻曾经接触过沙士患者的而在中国内地,有报告显示当时要出动警力去控制受检疫之人,限制出入,在私人住宅安装监视镜头,对违反者作严厉处处分包括死刑。
当有新发呼吸道传染病出现的时候,在未有有效的药物及疫苗出现之前,公共卫生措施如隔离,检疫以及限制社交等,都可有效地减少疾病传播,减慢社区大爆发的发生,减少个人对个人,家庭,病人复康,社会经济及医疗系统服务的长远影响。当然关注个人卫生亦同样重要,试想想如果有人都适当地放在口罩和保持手部卫生,各人都在自己的“微生态环境”(micro-ecosystem)成为自己环境的“自我检疫者”,防疫产生便能够相得益彰。
我相信检疫措施这个公共卫生的工具在社会整合间将会不断的讨论,但其于对付新发传染病控制的本质是无可置疑的。要释除公众对检疫行动的疑虑,透过频密透明和全面沟通是缺一不可的。政府市民上下一心,携手抗疫,视为上策。
转载自《信报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