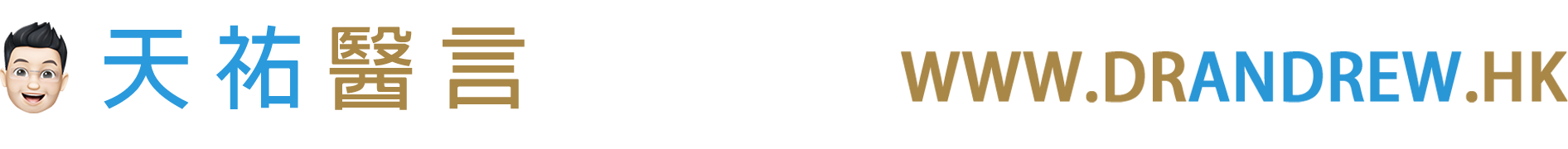「檢疫」和「隔離」有何不同?
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 會長
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 黃天祐醫生
要有效控制傳染病蔓延,公共衛生學常用的兩個風險管理的措施 為「檢疫」和「隔離」,其實兩者是有什麼分別?
近期,在2020年初的檢疫例子包括:
1.自二月八日之起,從中國內地來港之人士須進行家居檢疫14天;
2.停泊在日本橫檳的「鑽石公主號」郵輪乘客在船上進行檢疫;
3.外國包機從武漢撤僑,回國後國民須在檢疫中心或當地軍營進行檢疫14天。
而隔離例子包括:
1.懷疑及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的人士須在醫院內隔離及進行治療
2.正在接受檢疫之人士出現病徵時,需向有關方面求助,以作出隔離及診斷的安排。
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,檢疫是針對一些沒有症狀的人,但他們曾密切接觸確診或疑似的患者;或他們曾到訪傳染病發病率較高的地區。檢疫的目的為了將他們與其他人分隔以及限制他們的行動範圍。如果他們不幸出現病徵,可以將他們及早隔離接受治療,以避免繼續傳染其他人。基本上,為了確認曾暴露於發生傳染的地方之人士,在此傳染病的潛伏期內觀察此人士會否發病,從而減少接觸其他人的傳染機會。廣義來說,檢疫亦是一項可包括動物和貨物流動限制的衛生措施。
其實,檢疫措施在20世紀後期已逐漸減少用作大規模地用作防控傳染病工具,但由於新發病毒及傳染病大流行如2003年的沙士、2012年中東呼吸綜合症、2014年伊波拉病毒等等,國際間都使用了不同程度的檢疫措施,並配合達致公共衛生水平以及臨床的控制措施以控制疫情爆發。因為檢疫包含限制及禁閉,所以很容易令人聯想到人權和人身自由的問題,怎樣在公共衛生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?當事件涉及和影響公眾安全,我們就要衡量自由與人身安全的重要性。
推行檢疫這措施的歷史可追溯到1377年,當時沒有有效藥物可以控制醫治大規模的鼠疫,及18世紀後期用於處理霍亂疫情和20世紀初期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。在歷史上所有的檢疫行動和控制往往帶有歧視,因為當時的生活水平、醫療科技、藥物診斷等等都並未成熟,低下階層以及社會邊緣化之人士往往容易被標籤為傳播者,他們在毫無選擇下被禁閉於環境極差的地方隔離,所以這些人們都設法逃命離開,反而激增了疾病的散播。
誠然,現今的衛生檢疫不可跟歷史的方式同日而語,現時的措施是根據公共衛生的框架有效地執行,盡量根據流行病學的實證和科學標準,雖然在疫症蔓延的初期有很多變數,所以措施亦要不斷更新,以迎合對抗疫情需要;措施通常亦希望將被檢疫者之人數減至最少。話雖如此,被檢疫的人士的日常生活及社交活動、生理心理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。簡單的例如不能如常上班,影響收入;需照顧者如老人及小童怎樣得到適切的照顧等等,這些很實際的生活問題,都要在計劃實行檢疫措施時作周全的考慮。此外,研究都顯示出,從17年前沙士疫情中,分別在香港及加拿大多倫多接受檢疫的人士,一部分人都出現了一些負面情緒,甚至患上創傷後遺症等心理問題。
另外值得再探討的問題是,在一個公平社會裏,當一小部份人的人身權利被犧牲以保障其他人之公共衛生時,是否應有一既定機制,來補償這些被檢疫人士在金錢或非金錢上的損失呢?雖然各國檢疫往往有當地的法律基礎去支持,但實際實行措施時,不同政府用不同手法,以2003年沙士為例,當時加拿大是勸喻曾經接觸過沙士患者的密切接觸人士作自願檢疫。而在中國內地,有報告顯示當時要出動警力去控制受檢疫之人士,限制出入,在私人住宅安裝監察鏡頭,對違反者作嚴厲處分包括死刑。
當有新發呼吸道傳染病出現的時候,在未有有效的藥物及疫苗出現之前,公共衛生措施如隔離、檢疫以及限制社交等,都可有效地減少疾病傳播,減慢社區大爆發的發生,減少疫情對個人、家庭、病人復康、社會經濟及醫療系統服務的長遠影響。當然注重個人衛生亦同樣重要,試想想如果所有人都適當地佩戴口罩和保持手部衛生,各人都在自己的「微生態環境」(micro-ecosystem) 成為自己環境的「自我檢疫者」,防疫成效便能夠相得益彰。
轉載自《信報》